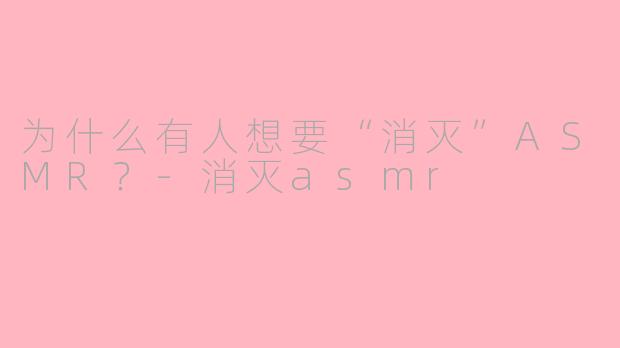这里的“消灭”并非指真正地取缔,而更像是一种对特定文化现象的调侃或反思。主要源于几种心态:一部分人无法感知ASMR的“颅内高潮”,将其视为无意义的噪音,甚至因细微声响产生不适(称为“音素触发”);另一些人则反感ASMR内容的过度商业化,比如刻意的表演、软色情暗示或快餐式内容稀释了早期ASMR的纯粹性。这种“消灭”的诉求,实则是对信息过载时代下内容质量与真实性的拷问,也揭示了感官体验的极端个人化——有人视作精神按摩,有人如坐针毡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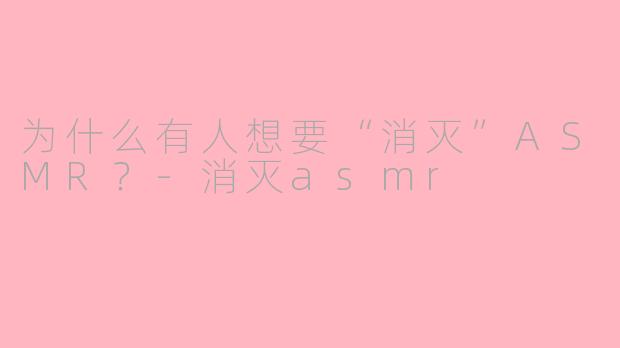
这里的“消灭”并非指真正地取缔,而更像是一种对特定文化现象的调侃或反思。主要源于几种心态:一部分人无法感知ASMR的“颅内高潮”,将其视为无意义的噪音,甚至因细微声响产生不适(称为“音素触发”);另一些人则反感ASMR内容的过度商业化,比如刻意的表演、软色情暗示或快餐式内容稀释了早期ASMR的纯粹性。这种“消灭”的诉求,实则是对信息过载时代下内容质量与真实性的拷问,也揭示了感官体验的极端个人化——有人视作精神按摩,有人如坐针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