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个被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充斥的时代,ASMR(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)仿佛一夜之间席卷了网络。屏幕上,人们对着麦克风窃窃私语、轻敲物品、咀嚼食物,试图通过特定的声音触发听众的"颅内高潮"。许多人从中获得放松,甚至依赖它入眠。然而,在这片治愈的声浪中,我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反感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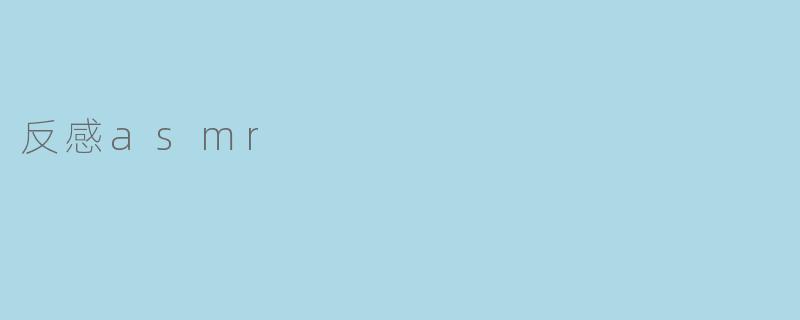
对我而言,ASMR非但不能带来放松,反而像是一种温柔的折磨。那些被刻意放大的耳语,总让我联想到蚊蚋在耳边嗡鸣,非但没有安抚,反而激起一阵生理性的烦躁;那些摩擦、抓挠的声响,仿佛无形的指甲划过心头,留下细微却持续的不适。我理解有人能从中获得愉悦,但我的神经似乎与这种刺激天生不合——它像一场强加于感官的细雨,本应滋润,却只让我感到潮湿的黏腻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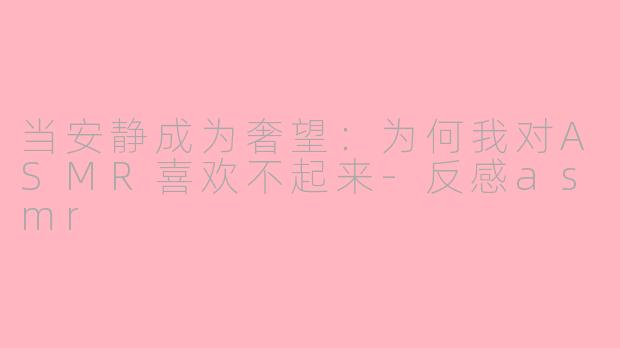
更让我困惑的是,ASMR常常被包装成"治愈焦虑的良药"。当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你应该通过某种特定方式放松时,你的不喜欢反而成了需要解释的异类。这种"被治愈"的压迫感,让简单的个人偏好变成了沉默的抵抗。为什么安静本身不再足够?当我们需要通过电子设备里的陌生人制造的声音来寻找平静时,是否也折射出这个时代对真实宁静的某种失落?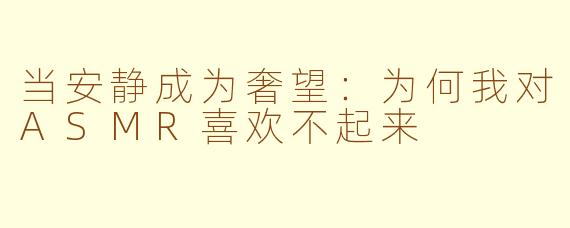
也许,我对ASMR的反感,本质上是对过度刺激世界的一种本能防御。在已经足够嘈杂的生活里,我需要的是真正的寂静,是思绪可以自由流淌而不被引导的空间。那些精心设计的声音触发点,无论多么"柔和",本质上仍是又一种对注意力的攫取。
说到底,声音的偏好如同味觉,本就极其私人。有人沉醉于ASMR的细微声响,也有人如我般向往"此时无声胜有声"的境地。在这个推崇多元的时代,也许我们更需要承认:不喜欢ASMR,不需要特别的理由。它只是证明,在寻找内心平静的旅途上,有人需要声音的陪伴,而有人,只需要自己的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