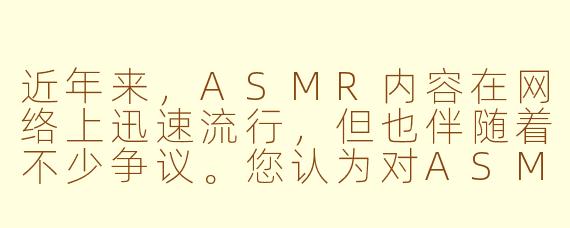对ASMR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。首先,从感官科学角度,部分研究表明ASMR的“颅内高潮”效应缺乏神经学共识,其效果可能源于安慰剂效应或主观心理暗示。其次,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质疑,许多视频打着ASMR旗号实为软色情或商业营销,如咀嚼食物、耳语挑逗等行为被指责物化感官体验。更深层来看,这反映了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异化——当私人化的放松方式被包装成标准化商品,当治愈需求被算法流量裹挟,我们实际上是在用消费主义方式解决精神焦虑。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言,这种“积极自我剥削”恰恰掩盖了社会集体性倦怠的结构性成因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类批评本身也构成文化博弈:传统对“严肃娱乐”的界定正在被挑战,而ASMR争议本质是关于数字时代感官伦理边界的重要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