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年前,ASMR(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)内容在B站掀起一阵风潮。UP主们通过细腻的耳语、敲击声、环境白噪音等触发音,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放松体验,视频播放量动辄百万,弹幕区满是“颅内高潮”“秒睡神器”的惊叹。然而随着平台监管收紧、内容同质化加剧,这一小众文化逐渐褪去光环,留下的不仅是“助眠神器”的标签,更折射出亚文化在流量时代的生存困境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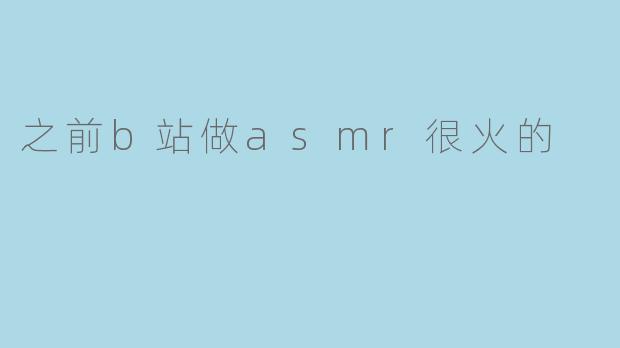
ASMR在B站的走红,最初源于其精准切中了当代年轻人的“睡眠焦虑”与情感需求。高压生活下,用户渴望通过沉浸式声音获得短暂逃离,而UP主们创造的亲密互动感(如“虚拟女友”“掏耳朵模拟”)进一步强化了情感联结。2018-2020年间,头部ASMR创作者如“MTkoala”“轩子巨2兔”甚至跨界出圈,引发大众对“声音经济”的讨论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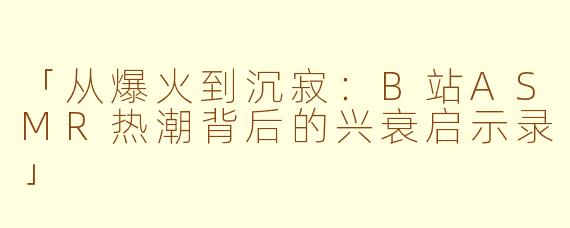
但繁荣背后暗藏危机。部分打擦边球的“软色情”内容招致争议,平台最终以“内容整改”为由大规模下架视频;同时,创意枯竭导致多数视频沦为“剪刀划快递盒”的流水线产物,用户新鲜感消退。更关键的是,ASMR的强依赖性与低变现能力让创作者难以持续——当“助眠”变成功能化需求,观众更倾向于转向专业音频平台,而非停留于娱乐社区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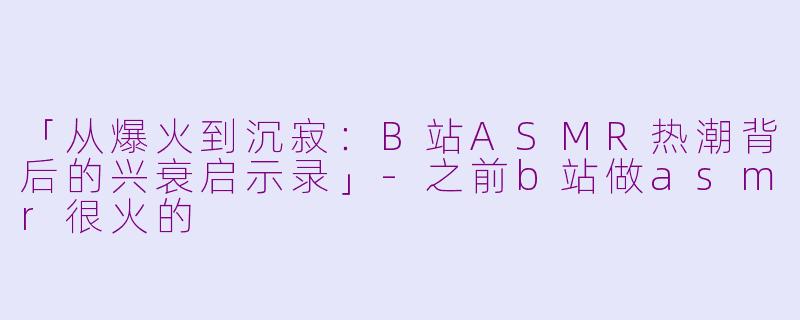
如今B站搜索“ASMR”,结果多是搬运视频或科普解析,昔日顶流UP主纷纷转型生活Vlog或游戏解说。这场短暂的热潮像一场实验,验证了亚文化破圈的两种结局:或被流量反噬,或在妥协中寻找新形态。或许正如一条高赞评论所说:“我们怀念的不是ASMR本身,而是那个还能被细微声音治愈的自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