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机里传来铁门缓缓关闭的沉闷回响,我蜷缩在虚拟避难所的角落。远处断续的呜咽声由远及近,指甲刮擦金属管道的刺耳噪音突然炸响——丧尸来了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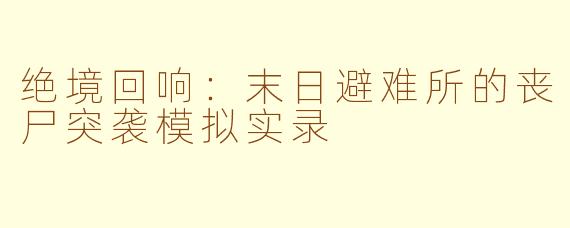
我调整呼吸,模拟手电筒开关发出“咔哒”轻响。光束扫过布满灰尘的储物架,玻璃药瓶相互碰撞叮咚作响。就在这时,货架后方传来拖沓的脚步声,混杂着液体滴落的黏腻声响。我迅速关闭手电,黑暗中,自己的心跳声通过骨传导耳机放大成擂鼓般的震动。
丧尸的低吼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左侧通风管道传来密集的抓挠声,像无数甲虫在铁皮上爬行;右侧的木板突然爆裂,木屑飞溅的碎裂声清晰可辨。我摸索到一根铁管,金属与水泥地摩擦发出令人牙酸的尖啸。当第一个丧尸扑来时,腐烂衣物撕裂的纤维声几乎贴着耳膜炸开。
我抡起铁管,击中肉体的闷响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咔嚓声在颅腔内共振。粘稠液体溅到墙壁上,滴答滴答落在积水洼里。更多脚步声聚集而来,我踉跄后退时踢翻了铁桶,空桶滚动的轰鸣在密闭空间里不断回荡。丧尸群逼近的声浪形成包围圈,它们的呼吸声像破旧风箱般重叠交织。
就在嘶吼声几乎将我吞没时,我摸到了紧急通道的门把手。生锈铰链发出长达十秒的尖锐悲鸣,我冲进雨夜。倾盆大雨瞬间淹没所有声音,只有自己的喘息在雨中起伏。远处传来最后一声丧尸撞上铁门的巨响,余韵在雨幕中震颤消散。
我摘下耳机,房间的寂静突然变得陌生。指尖残留着幻痛,耳蜗里仍萦绕着那个世界的回声。这场二十六分钟的声景实验让我明白:最深的恐惧,往往诞生于声音构筑的想象牢笼之中。而当我们关闭模拟器,重新听见现实世界空调的嗡鸣、键盘的敲击声时,那种重返人间的庆幸感,或许正是这种极端体验赠予我们的、关于平凡的珍贵启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