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,ASMR(AutonomousSensoryMeridianResponse)作为一种通过特定声音触发愉悦感官体验的现象风靡全球。而“ASMR音译”这一概念,既指其从英文缩写到中文“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”的术语转化,也暗含了跨文化传播中声音符号的重新诠释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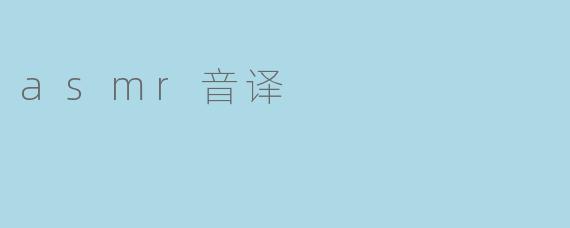
从“沙沙的耳语”到“咀嚼声的治愈力”,ASMR的视听内容在中文网络中被赋予“颅内高潮”“耳音按摩”等本土化标签。音译不仅是语言的转写,更折射出文化认知的差异——西方强调生理反应的科学性,而中文语境更倾向诗意化的感官描述。例如,“Tingles”被译为“酥麻感”,既保留原意,又融入东方人对身体知觉的细腻表达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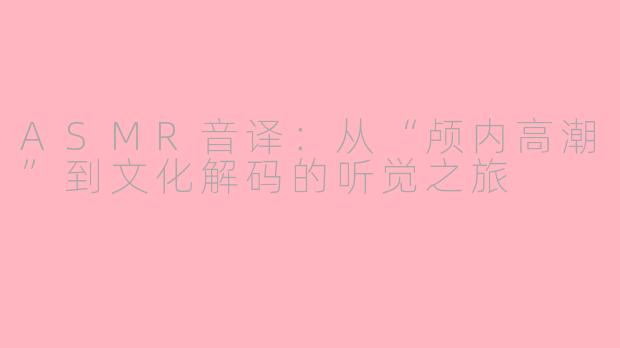
ASMR音译的争议同样有趣:反对者认为直译丧失原味,支持者则主张本土化能降低认知门槛。这种争论背后,实则是声音疗愈文化的全球流动与在地适应。当“敲击键盘声”在东京被称为“コンコン音”,在北京变成“解压打字音”时,ASMR已超越听觉本身,成为一场关于语言、神经科学与大众心理的奇妙实验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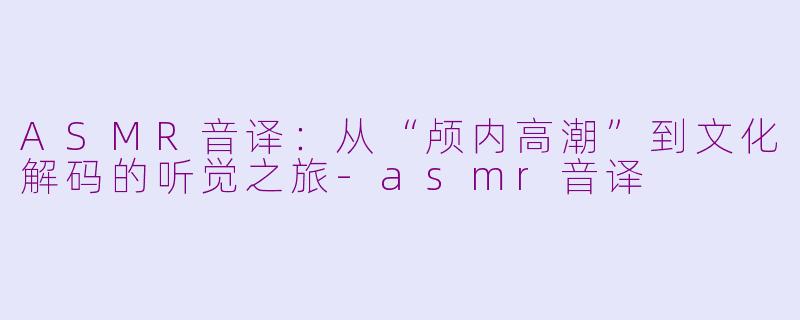
或许,ASMR音译的真正意义,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:当声音跨越国界,是否也在重构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