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,我关掉了第37个“耳语哄睡”视频,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屏幕上,博主正用指甲轻敲玻璃瓶,发出细碎的咔嗒声——这曾是我的睡前必修课,如今却像一场无休止的电子围猎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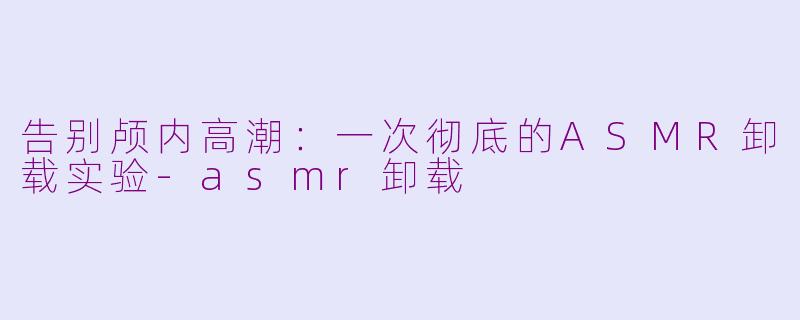
ASMR(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)曾是我对抗失眠的救命稻草。三年前,当第一个“理发店模拟”视频让我后颈泛起酥麻时,我以为找到了现代人的解压圣杯。但渐渐地,算法织成的温柔陷阱开始显形:收藏夹里堆叠着387个“触发音效”,耳机成了植入耳道的输液管,而我的注意力像被猫抓过的毛线团般支离破碎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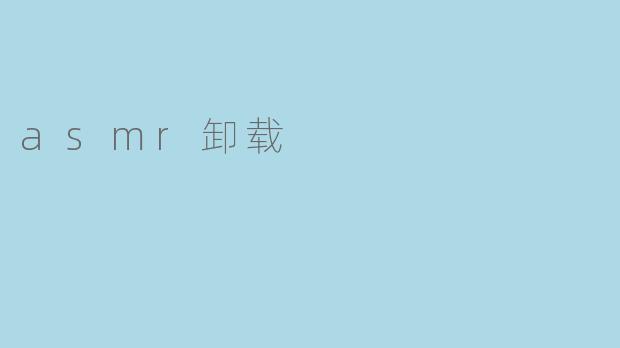
卸载行动始于一次数据清理。手机存储显示,某ASMR平台独占23.7GB内存,相当于468集《甄嬛传》的体量。更惊人的是屏幕使用时间——平均每晚97分钟在反复切换“雨声”“翻书声”“泡沫摩擦声”之间流逝。那些曾被称作“颅内按摩”的声波,如今像一群永不停歇的装修队,在我的神经回路上凿出凹痕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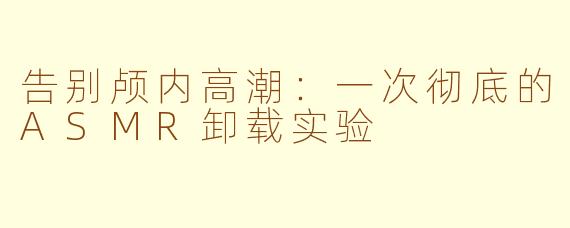
第一周戒断反应来得凶猛。没有耳边的碎纸声,夜晚安静得能听见血管搏动。但到第三周,某些变化悄然发生:久违的鸟鸣穿透晨雾,键盘敲击声竟自带韵律,连楼下小孩的哭闹都成了鲜活的生命力证明。原来真实世界的声谱里,本就藏着最精妙的ASMR。
现在,我的耳机盒积了薄灰。偶尔在便利店听见收银员清点硬币的脆响,还是会条件反射般脊背一颤——但这次,我选择让颤栗自然消散在空气里,像一片雪落在温热的掌心。卸载ASMR不是拒绝愉悦,而是把感官的遥控器,从算法手中夺回。